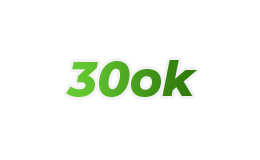
谁在唱,芳草凄凄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你教我轻轻地哼,红日落在山头,燃烧了整片枫林。“奶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眉毛一眨一眨,像隐隐约约的启明星。“这个呀,是离别的诗,囡囡长大了,就会懂。”奶奶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你教我轻轻地哼,红日落在山头,燃烧了整片枫林。“奶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眉毛一眨一眨,像隐隐约约的启明星。
“这个呀,是离别的诗,囡囡长大了,就会懂。”奶奶轻轻地笑,像怕惊了候鸟的湖,涟漪在奶奶脸上欢快地摇荡,迟迟没有褪去。从山冈飘来的蒲公英像岁月在一瞬间染白奶奶的发。我捉起一朵朵的小精灵,鼓起腮子又把它们吹向远方。然后它们像隔空的岁月一样变得渺茫。
“我抓……我抓…抓…抓到你了。”奶奶惊着从睡眠中醒来,握着我在空中胡乱狂舞的双手,她的微笑融在甜蜜的夜里,嗔道:“这孩子,又梦到什么了……”然后把我的双手环在她的脖子上,用粗糙又温暖的大手轻抚我的背,哼着我不知名的歌谣哄我睡去。
岁月,如箭,把我射向青春。
“奶奶奶奶,你看,我比你高了呢。”我和奶奶站成一排,倚在陈旧的黑色门框上,奶奶花白的发,没能没过我的耳际。她佝偻着身子,靠着我,轻轻地,像一棵千年古槐,落尽繁枝,枯着枝干在等风把它吹倒,那些鱼尾纹在她眉角再也不肯褪去,在风吹过的瞬间,从前的小鱼却越长越大,横在两颊,酒窝也不再那么清晰,和深深浅浅的鱼尾纹夹在一起,刻画下她衰老的痕迹。
“是呢是呢,囡囡长得比奶奶都高了。”她呵呵地笑着,像二月里盛开的迎春花。花白的发丝从耳际滑下,拂在她瘦削的额前。门前的桂花树像突然充气的气球,一瞬间从昨日的奄奄一息长成苍翠的大树,风拂动树梢,几朵细碎的桂花落下,我把它放在掌心,闻到了童年的味道。
日暮,又晨亮。花开落了许多个季节,然后又长出新芽。
我坐在四方的木架床上,奶奶带着肥大的老花眼镜,将我细碎的绣花裙折了又叠,,用手轻轻抚平折起的皱。我看着她在昏黄的灯下投在地上的影子,佝偻成一片孤独的芭蕉叶,在风雨飘摇的夜晚用灰蒙的视力认真地折叠我明年夏天要穿的衣物。
明日,天亮,雨停,风不摇。
我拖着长长的行李箱,两只轮子在地板上轻轻地压出吱呀声,像疼痛了不愿再走的小孩。窗子朝外打开,用硬直的铁丝支着。奶奶拄着拐杖,视线锁在藤条做的秋千上。那里有我迎着风掉落下来的笑声,有跌了屁股后大声号啕着要糖吃的童稚,有奶奶用手心里遗落下的温暖,和我不经意间绾下的童年。
“奶奶。”我轻轻地,像从窗边溜进来轻轻拂动发丝的那抹风。走过去,握紧她的手,凉的,有几点亮晶晶的液体。舌尖触点,咸的。
“奶奶,奶奶的囡囡就要去读大学了呢。”我把她额前的头发拂上耳际,风在一瞬间风干晶莹的两颊,然后把心情抚平。她干瘪的嘴唇,在空气中蠕动,想要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她攥紧我的手,瘦削的关节像商店里展出的骷髅头,我感到疼痛,却不是手,是左心房那颗日夜跳动的东西。她的眼袋有些饱满,却没有雨水落下,她又努力掰开我的手,横横竖竖画了几笔,是“乖”。
我点点头,她拉着我走向门口,抬起头看阳光照射在我脸上映出清晰的轮廓,然后慢慢松手,目光还锁在我豆蔻年华的脸庞,像看着自己心爱的风筝被风吹走。她的手抬起,又放下,她想再摸摸我蓬乱的发丝,但她已经,够不着了。我握着她放下的手,迎着阳光,笑着说,轮到我摸你了。亮闪闪的牙齿把阳光都反射在她眼睛里,像星星一样闪亮。
她笑了,也点点头。漏风的门牙像孤立无援海岸边突兀的石头,住在她苍老的牙床上。
“我走了。”我拖出长长的行李箱,跨出门口,我不想,她饱满的眼袋,装满了雨水那么辛苦的忍耐。我迎着朝阳的方向,风窜进我的眼睛,倒出了咸涩的雨水。我不敢回头,因为感觉告诉我,奶奶的眼睛,已濡湿了我的背影。
更漏子,滴滴,过天明。
我焚起香,烟像昨日一样由清晰到飘渺。苍柏上有只黄鹂在轻轻地哼唱,像谁沙哑了嗓子。记忆像飘浮的蒲公英一样四外散落,粘在泥土里,再也捡不起来。
我站在奶奶的坟前,独自回忆着往事的一幕幕,我浮在深深浅浅的回忆里,努力回游,却再也找不到握着另一半回忆的某人。像拿着五百万的借据,在人海茫茫中再也找不出欠债的那人一样失落。
我捧着白色的菊花。“奶奶,你还教我吟诗么?我知道了那词的下阙,‘明月楼高休独倚,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真是一首离别的诗呢,是么?”没有人回答我,万籁俱寂,坟前又飘起白茫茫的蒲公英,像奶奶花白的头发,被风随意地扬起。
咸涩的雨在我两颊滑下,回忆搁在窗台,看着我一人站在舞台,独自谢幕。
谢幕的尾声,回忆在唱,芳草凄凄……
版权声明:本文由30ok网通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链接:https://www.renyuechuanqi.com/html/sanwen/x6sidsi861yyg.html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