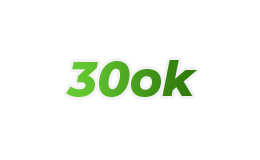
父亲的脚
腊月二十五的清晨,我还躺在被窝里,就听见楼下传来断断续续的熟悉的敲门声。那种敲门声很特别,因为发出声音的不是木门,而是门框。父亲还是那样的爱惜每一件家里的东西,几十年的辛苦让他养成了对东西近乎小气的习
腊月二十五的清晨,我还躺在被窝里,就听见楼下传来断断续续的熟悉的敲门声。那种敲门声很特别,因为发出声音的不是木门,而是门框。父亲还是那样的爱惜每一件家里的东西,几十年的辛苦让他养成了对东西近乎小气的习惯。是爸爸回来了,我想。我摸索着床头的墙面,试图打开灯,但没有成功。窗外晨雾迷蒙,我伸出去的手臂能清楚的感受到来自窗外的冰凉。我仿佛看见父亲正一瘸一拐的从窗外走来,没有一丝言语,脸上说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我知道,父亲回到家之后,邻里只要看见了都会说上一句:“嗯,看起来,你的腿好了很多嘛。”或许是恭维,或许是祝愿,又或许父亲的腿真的好了很多。我不愿去想象出事当天的情形,更不愿揣测父亲母亲那段日子的心情。可每当想到或听到“父亲”两个字,所有的事就像是肆意的洪水,从记忆的决堤口汹涌而出,让人猝不及防。
听母亲后来提及,父亲出事的那天是村里父亲的一位朋友一直陪在他的身旁,直到将父亲被送到州医院他才离去。仔细回忆起来,那天的天气十分晴朗,万里无云的天空没有焦灼的迹象。群山环抱的村庄虽然朴素无比,却也十分宁静祥和。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夏日,踏着清晨的露水早早的就离家前去村里的一个司机师傅家帮忙。那天一定很冷清,前去帮忙的乡里应该很少,否则看见父亲忽然倒地而伸出援手的人为什么会只有一个人。母亲说,父亲被打砂的机器打断了右腿,整只右脚血肉模糊,踝关节以下只剩下一张皮还连着上下两部分。父亲只记得自己的右脚突然一麻,然后就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父亲的朋友一直抱着他的上身,并且试图遮住他的眼睛。但那时的父亲早已经明白了一切,事实上没有人比父亲更了解当时的情形。父亲没有坚持要求拿开眼睛上的衣服,只是默默的流泪。他哭着自言自语道:“我的脚没了,人废了,孩子也废了……”。父亲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这几句话,周围的人也情不自禁的跟着落泪。
得知父亲出事的消息是在高考的最后一天下午,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母亲告诉我的时候,父亲已经出院。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周末,我有给母亲打过一次电话,还记得电话那边十分吵闹,母亲扬着嗓门解释,说她正在村里的一户人家里吃酒。曾听说过很多父母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而将如父亲或母亲去世、出车祸、遭遇大灾难的情况隐瞒下来的故事,而且在小说中也被写了无数遍,但始终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活生生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母亲将事情的原委完完整整的告诉我的时候,我竟然有一种未卜先知的感觉,仿佛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所有的父母对孩子都有同样重量的爱,而这种爱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麻木,变得甚至一度认为那是理所应当。
父亲生在农村,却长在建设家乡、打工赚钱的路上。父亲时常说,他们这一代人是含着泪活过来的。虽说有幸生在和平年代,但也遇上了和平年代最为重要的建设时期。算算父亲成家立业的年纪,正好碰上农村大搞基础建设,建土坯房、拉电线、修公路,我们这一代人所享受的东西都是父亲一代辛勤付出的结果。凭着不到二年级的知识在外奋斗,而今的我根本无法想象他是如何走过那风雨交加的四十年的。父亲结婚的时候,从爷爷那里分的了两亩地,一块腊肉和三百斤白炭。之后的家业全是父亲母亲用汗水铺砌,用脚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每一寸墙,每一扇窗;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件衣服,每一床被子,上面都留有父亲的脚印。父亲是在用自己的脚丈量着自己和煤窑之间的距离,用自己的脚计算着自己生命的长度和宽度,用自己的脚支撑着这个并不算富裕的家走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父亲的大半生都是靠着双脚走过来的,他用他的双脚不仅走过自己的人生,也同样支撑着我们的世界。对于依赖双脚奋斗的人却在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少了一只脚,他的世界糟糕到什么程度旁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不仅他的世界塌了半边天,这个不算富裕的家也跟着塌了半边天。父亲病重期间,母亲天天以泪洗面,将仅有的一点微笑留给了当时还在复习备考的我。
窗外似乎下起了小雨,远方的山峦模糊的只剩下一点轮廓。母亲亮了灯,楼下渐渐多了些说话声。没过多大一会儿,我就听见母亲在楼下叫我起床。“快起来了,来客了。”母亲喊道。哦!来客了,确实来客了!
版权声明:本文由30ok网通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链接:https://www.renyuechuanqi.com/html/sanwen/x5udi85us0t1h.html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