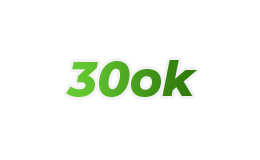
我的至爱亲朋(9):南方有一抹青绿的记忆
母亲说大姑来电话了,猛一楞,一时没有想起母亲说的大姑是谁。大姑是父亲的姐姐,在我的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个年老的女人,比现在的母亲还要老的女人。可我见着她时,她应该不会超过五十岁,现如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母亲说大姑来电话了,猛一楞,一时没有想起母亲说的大姑是谁。大姑是父亲的姐姐,在我的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个年老的女人,比现在的母亲还要老的女人。可我见着她时,她应该不会超过五十岁,现如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五十岁的女人绝不会和年老这个词挂起钩来。
可大姑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一个年老的女人。
那一年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回老家——一个南方小山村。
南方的冬天,满山的绿颠覆了我印象中寻常的冬天,北方的冬天,只有呼啸的风和一排排挺立着但枯干了枝桠的树。而南方,注满了水的稻田像是一面大大的镜子,映着低矮的天空越发的低矮,像是要扑进水面似的。
叔叔的家座落在一面半山坡上,离着不远还有几家人,那些高大或者低矮但生长都很茂盛的植物在房前屋后次第的展示着它们的身姿,大多我叫不上名字,总是跟在堂姐身后问东问西,堂姐总是很有耐心的说给我听,有些方言我听不懂,急起来跟她嚷,她也不恼,笑着嘀咕着什么。第一次去大姑家就是跟着堂姐一道去的。
大姑家离叔叔家大约有两三里地,要翻过一道山坡,坡上有斜斜的便道,铺着秋天时掉落的叶子,因为潮湿,枯黄的叶片还很柔软,脚踩在上面像是踩在厚厚的毯子上,一溜小跑下来,站不稳,一不留神,我一下栽进道旁不知什么人挖的深沟里,好在沟里也铺着厚厚的落叶,不至于摔坏,可我的脸上头上沾满了叶子和细枝,活像蹲坑的。姐姐站在沟旁幸灾乐祸的前仰后俯的大笑着,堂姐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使劲憋着,撑不住劲我大声哭起来,这样一来,她们俩才七手八脚的把我拉上来。没等我擦干脸上的泪,三个人又你追我赶的跑起来。
大姑的家在山洼的低矮处,门前是一片开阔地,不算小的院落,显出家道的富足。离着还有十好几米,堂姐就扯开嗓门叫起来:娘娘(niāng)——。她的声音尖脆清亮。听到声音,院门响处,一个中年男人一边开门一边高声斥责着吠叫的狗儿,我和姐姐吓得跟在堂姐身后擦着边儿进了屋子。
虽然是正午,屋子里还是很暗,堂姐恭敬的对跟进来的中年男人介绍着我和姐姐。
“这两个娃儿,老早就听说你们到了,才来看我撒。”中年男人的口气中透着一丝的不满,从一见面我就莫名的不喜欢他。
堂姐说这是姑爹。我和姐姐“唔”了一声算做答应了。姑爹的脸上有明显的不高兴的神气。
堂姐领着我和姐姐进了堂屋西侧的一间偏厦,那儿是厨房。厨房也和整个屋子一样的暗沉,堂姐站在门边朝里喊着:“娘娘,有客人来喽。”声音虽然不像刚才那样尖脆却依然清亮。
“快进来,是不是小玲和小云来了?”
那就是我见着大姑的第一面,头发稍有些凌乱的在脑后扎成一把,脸上布满了细碎的皱纹,身上是一件深灰色的棉而衣服,沾着灶间的灰尖。她的怀里是一个五六岁大的男孩子,面对我们的注视,仍然没有松开正噙着的乳头。
这便是大姑,一个不到五十就年老体衰的女人。
那天,我们就坐在灶间应答着大姑的话,大姑抓着我和姐姐的手一遍一遍的抚摸着,又一遍遍的说:“娃儿呀,你爸爸从小苦命,你们长大一定要好好孝敬他。”
到走的时候,看到大姑眼里噙了泪水,其间,她怀里的孩子一刻也没有松开嘴。
堂姐说,那是大姑四十多岁得的老儿子,宝贝的不得了,都六岁了还没断奶。姑爹在村里有些能耐,在家里对大姑从没有好声气,有时甚至还动手打大姑。姑姑家的大儿子也和父亲一个样,对大姑动不动就横鼻子竖眼的。姑爹对大姑娘家的人一点儿也不亲近,似乎还带着不满,所以,直到离开,我和姐姐再也没有去过大姑家。
后来,父亲退休后回老家小住,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说是姑爹游说父亲去开他家的小客车,让我们写封信劝劝姑爹。父亲原本就是因病提前退休的,回去小住也是为了调养调养,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姐姐连夜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没想到,姑爹回信倒把我和姐姐大骂一通,说他好吃好喝的待父亲,我们却横竖不领情。我们不知道姑爹和叔叔谁在说谎,只好让父亲尽快回来。父亲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那以后,也再没有和大姑一家有任何的联系,只是给叔叔去了封信,报了父亲的丧讯。
母亲以前很少提起父亲家里的人,现在,也许是老了,留在记忆中的事渐渐变得美好起来,跟我们说起大姑时,脸上泛着由衷的怀念。
母亲告诉我们大姑来电话说,姑爹已经不在了,前些年得了癌症去世了。
想来,现在的大姑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年女人了,她应该能与我脑海里存着的印象完全重叠起来吧,她还是我见过的那个样子呢。
忽然的,很有些想念起她来。那只拉着我的和姐姐不住抚摸的粗糙的手。
版权声明:本文由30ok网通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链接:https://www.renyuechuanqi.com/html/sanwen/loddu5ios52tf.html
上一篇:雨幕中的身影
下一篇:北方春天的行走(2)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