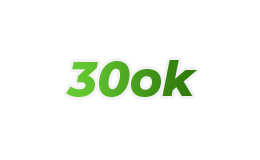
蛮舅
蹲在厕所里,看着黑不隆冬的下水口。倏然间,想起了蛮舅,想起蛮舅给我捞手机那件事情。那年,年过半百孤身一人的蛮舅来帮单位打扫卫生。一天,不小心把手机滑落掉进厕所下水口里,蛮舅不声不响到街上买来一根竹竿
蹲在厕所里,看着黑不隆冬的下水口。倏然间,想起了蛮舅,想起蛮舅给我捞手机那件事情。
那年,年过半百孤身一人的蛮舅来帮单位打扫卫生。一天,不小心把手机滑落掉进厕所下水口里,蛮舅不声不响到街上买来一根竹竿,用一节铁丝扭成弯弯的挂钩在竹竿顶端。见状我问他做甚?他说我挨你捞手机,任凭你如何劝说,手机一旦掉进水里浸泡,就算是捞上来已经是不能用的了,可他就是认个死理,一个劲地趴在厕所里摸摸索索整了个老半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一个劲地说;你们这厕所干净得很,比我们的家屋要干净几十倍,不脏的。只可惜就是捞不到,连碰都没碰到一哈,可惜了,可惜了……。
望着蛮舅无奈而失落的样子,我的心一阵紧缩,汩汩酸楚袭上心来。至今终没明白那时究竟是对蛮舅的感动,还是对他忠厚的怜悯,亦或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情深深地咬噬着我的善良。
其实,蛮舅只来到单位一个月。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走了,要到外地下井挖矿石,在那里虽然有危险,但是可以多挣点钱,留用着将来养老。无论我如何挽留,如何劝导,蛮舅还是走了,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帮人下井采矿,带着多挣钱的目的,带着积攒养老钱的理想。走了,在一个海雾弥漫的清晨,孤身一人。
蛮舅,这是我按辈分对他的称呼。他真正的姓名叫付成林,但家乡里的人一律都叫他的乳名“蛮子”。蛮舅一生平常得微乎其微,自幼丧父,忠厚老实。日常里一般不声不响,说起话来两腮微笑,慢慢悠悠,把声音拉得长长的。记得小时候我们放学要经过他家一块土地,姊妹几个总喜欢逗逗他玩,刻意学着他的腔调远远地喊道;蛮舅,我们要克你家吃饭了,你家有饭吗。他停住活路,抬起头来笑笑,尔后一贯性地拉长腔调说;呜呜……要得,饭嘛有的是。
家乡里村村组组之间,乡亲邻里之间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所以,家家户户都喜欢点请他帮农活,他做活路不偷懒也不寻闲,实打实一心眼做事。在乡邻里间他是善良诚实的象征,是忠厚巴适的楷模,一个实实在在的心眼使得好心人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于是,他有了老婆,有了属于他的那个家,再后来有了女儿。家乡人说他是幸运的,而我总觉得蛮舅命运多舛,是不幸的。蛮舅自幼丧父,家境贫寒,虽得妻室儿女,却断后(无生育能力),可有谁真正知道他寡言少语的背后,他内心的欢乐有多少,他无言的苦衷有多难,他命运的悲哀有多重!
婚后数年不见丁香,老婆终于红杏出墙,竟然跟了他的妹夫私生了女儿。有人悄悄地告诉他实情,他总是沉默了很久以后平静地说;“哪个敢在羊群里来认找羊啊”。其实,蛮舅心里很是明白的,他用他的忠厚善良与忍耐包容了一切,保全了他的家,诠释了他的人品。可是,到最后他的老婆变本加厉,连娘带儿弃家而去,丢下他孤独一人,丢下那间低矮潮湿,被烟熏火燎得黢黑的瓦屋。蛮舅呢,他用忠厚善良与忍耐包容赢得的只是;人走楼空,一生都没有保全的家,那个破败不堪的老瓦屋,落得个鸡飞蛋打,提篮打水一场空。
从那以后,本就不善言语的蛮舅更加沉默了,颓废得死寂一般地沉默。没有沉默中爆发的能量,却萌生了丢家外出流浪的“勇气”,一走很多年音信渺无,留下那间矮小而破败不堪的瓦屋孤孤独独地盘坐在山湾边,只有屋檐下的蜘蛛不弃不离,把网织得密密麻麻严严实实地封住了早已不见本色,罅了很大裂缝的木门,只有周围墙洞里的谷雀逐年添丁增口,似乎依稀可见那个弃家而去的老婆,把鼻涕擤了甩在门墩上的痕迹。门前的杏儿树开花又结果,落叶又开花,周而复始地轮回着,就是死寂一般地沉默,总撩人寂寥荒凉伴着阴森。如此,时间流逝着许多年,人们似乎渐渐地把蛮舅忘记掉了,也很少有人再提起。
有一天,消逝多年的蛮舅突然回到家乡,依然孤身一人,好不惨淡。但是直扑的村里人带给他的问候,就是似乎悬念了几辈人的一句话;蛮子,你还活着啊?这么多年你到底去了哪里,做什么了,我们都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几个年长的老婆婆以泪泡话,揉脸抹泪地望个不停左瞅瞅,又看看,前拉拉,后扯扯地问够不休。蛮舅返乡那穷酸的惨状苏醒了她们的记忆;“蛮子是个好人呐,那个不得好死的绝婆娘啊,把你害得嫩个惨,呜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擤来甩得围观的人无心躲避,无意退让”。蛮舅惨淡地笑了笑,人们议论的嘈杂声淹没了他的回答,听不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挨近里层的人回头相互转告说,依旧那声呜呜……挣饭吃,饭嘛有的是。
一天,我告诉蛮舅,您年纪也渐渐大了,就到我们单位去帮打扫哈卫生,一个月给三百块生活钱,将就着过以后的日子吧,不要到处流浪了。他答应了,在家乡稍作停顿几天后就来到单位。他有时对我讲;秀,在这点好,吃饭不用愁。不比在老家,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的不自在。
但是,我总没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一个满足的会意,也可能我压根就没有刻意对蛮舅的生活为他寻找过什么。
一个月里,他总是在尽心尽职地忙活着,闲来没事就把回廊后面的空地翻挖出来,种点豆子、栽点包谷、培些葱葱、撒下芫荽,总是把那一小片土整的琳琅满目。不让自己闲下,也不容土地空着。一个月里,我根本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变化。说实话,压根就没去理解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更不知道他有没有欢乐,有没有苦衷,更没去想他有的什么悲哀。所以,当他告诉我他要走的决定后,我才恍然大悟;他的离开在他来之前就早已决定了的,只是为了赢得一份给我对他“照顾”的尊重,给他本就诚实的惯性更增添一层不语的报答。
他走了,在获得一份释然以后毅然决然地离去,去了很远的地方。到底去了哪里,仍然把一种悬念和未知,撂给还对他时不时想起的乡亲们,把一份深深的不安撂下给了我。
一年以后。
那天,老家来电话;蛮舅死了,客死他乡,千里之外的矿山,在他的租房内,死因不明。说是由公安机关寻根通知的,通知亲人前往领尸。
这个死讯重重地敲了我一棒,我的心紧紧地收缩着,眼泪不由得悠悠滑落下来,脑子里空空的不知所以。蛮舅的死讯紧紧地抓住我的心,在我的胸腔里打翻了五味瓶子,那段时日,总让我不识滋味,也不是滋味。
在我还未来得及回应的时候,老家又传来消息
版权声明:本文由30ok网通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链接:https://www.renyuechuanqi.com/html/xiaoshuo/xs7s5d7ougtt3.html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