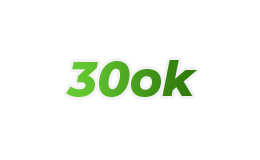
杀鸡磨刀
这几年的人让动物欺负怕了,它们隔三差五集体生病让人类感受恐怖。有消息说禽流感在新疆被发现,石泉的西单菜市场里已有所动作:那几个杀鸡磨刀的店家,整天把手插在口袋里,踱步子玩。没生意了!年关将近,禽流感已
这几年的人让动物欺负怕了,它们隔三差五集体生病让人类感受恐怖。有消息说禽流感在新疆被发现,石泉的西单菜市场里已有所动作:那几个杀鸡磨刀的店家,整天把手插在口袋里,踱步子玩。没生意了!年关将近,禽流感已被淡忘,而且可能已治愈了吧,这几天杀鸡磨刀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正如挂“吃饭补胎”牌子的酒家也兼卖茶叶、香菇一样,“杀鸡磨刀”并不仅仅两项业务。杀鸭杀鹅、烧腊肉、烧猪脚等杂活他们也干。但我从未见过他们磨刀,可能是晚间的业务吧。
前几天在乡下教书的舅老倌送来一只土鸡。这年头能吃上“绿色鸡”已是一种奢侈了。我一个大男人,却怕杀鸡。连杀鱼时都不敢用手拿,得用榔头拨拉,让它在水池壁上碰死。所谓“君子远庖厨”。找“杀鸡磨刀”吧。
“杀鸡磨刀”的门口有一个大塑料盆,里面摆满了待处理的猪腿。盆的旁边有几只鸡,腿被绑了,眼睛很痴呆。鸡周围的地上是一片污血和鸡毛。一个炉子上架着一口铁锅,铁锅里是翻腾的黑色沥青。几个猪腿被铁钩挂在开启的卷闸门下。老板手拿着一盏喷灯,火苗呼呼作响,喷向挂着的猪腿。这是在“燎毛”。猪腿有的地方已被烧焦,猪皮已焦,猪毛焉存!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儿,一手拿着斧头,一手从盆里捞出一只猪腿,“砰砰”几下,“猪鞋”就被脱下了。真是熟练。他把猪腿放入沥青锅,用一只勺子舀上沥青,浇淋未淹到的部分。他拿着猪腿端部,冻得通红的手一刻也不松开,也不怕把手烫了!浇满沥青的猪腿经冷水一激,沥青壳象纸一样容易撕下,猪毛随之扯出带下。他用袖子在嘴前快速一拉,擦掉了清鼻涕。他的脏旧的书包在斜放的锅盖上,随时都要掉的样子。想我那温室里的儿子,长到这个年龄时,不知能不能帮猪“脱鞋”。
一个女人,应该是老板娘,在一旁洗着猪腿和杀好的鸡。
穿着厚重黑色皮夹克的老板忙完猪腿,顺势撸起一只鸡。这鸡早都让先前同伴被宰的场面吓呆了,忘掉了踢腾和哀鸣。老板抓住“头发”向后一扯,使脖子鼓起。脖子上的毛经他两下扯掉,露出鸡皮疙瘩。下刀极轻快,如刀客(我不自主地摸了摸脖子)。血一条线,流到一只碗里了。也许知道离死亡只有几分钟了,鸡象征性地蹬了几下,血却因此流得更畅了。碰上“职业杀手”使鸡死的干净体面,是鸡的福。想起小时家里杀鸡,被剁了头的鸡满院子狂奔,那场面真是少儿不宜。
等血只是断断续续滴几滴时,鸡被扔在水缸和墙的夹缝中。我想它还有意识,但因为遭受的折腾,它已放弃用力,而是静静享受着如喝醉般的梦幻时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在猜度鸡的感受,而且断定猜得正确。
“你的鸡杀好了。”
老板娘的声音使我从鸡变回了人。
临走我问了一个问题:“这么多猪腿和鸡,都没打记号,你怎么分得清哪条腿是谁的?”老板娘看我外地口音,便笑着用普通话答到:“你们看不出,我们分得清,不会搞错。”
一行有一行的门道。
她也是外地口音。
我发现老板娘的脸上施了薄薄的粉。
版权声明:本文由30ok网通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链接:https://www.renyuechuanqi.com/html/sanwen/z4uou84o558ty.html
上一篇:病里乾坤
下一篇:【擂台赛第四期】那年情书
相关文章
